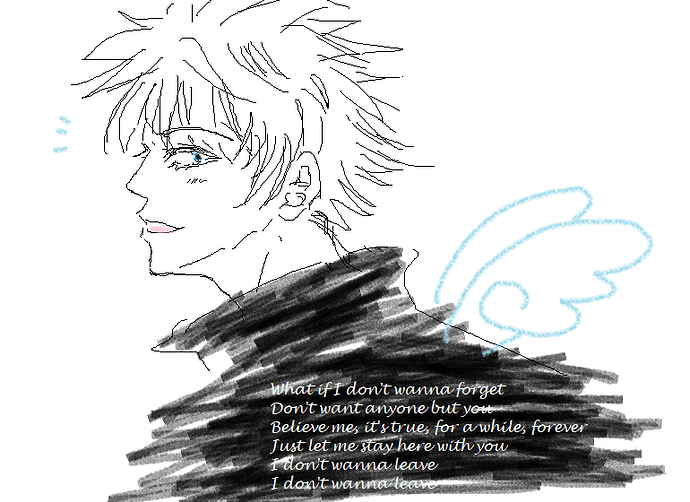※大约5.4K字,手边没正事的教祖教师厮混中(笑)
※有私设,脑内妄想勃发的教师悟,拿对方没办法的教祖杰w
※依旧一发完。也依旧是一款纯爱的教祖教师(自己觉得)
虹龙的报恩
即使不打开,那些绝望与希望也全部属于我。
真是的,别把人说成潘朵拉的箱子。
*
黑发的诅咒师如往常般堆着满面的假笑,来到富豪信徒的宅邸。这次只有信徒的妻小在家,两人将他视作拯救一家之主的恩人,不断地鞠躬作揖,说着夏油大人真是像菩萨一样的人。信徒年仅五岁的女儿天真无邪地摘下了院子里的小白花,双手呈向了眼前的男人。
此时豆大的雨点落下来,打湿了女孩的小手,孩子的母亲赶紧抱起她,一面道歉,一面往屋簷下移动。但是女孩仍然坚持把手中的花递向教祖大人,鼓着两颊,小脸都红了起来。
那不是存在于平地的野花,是带泪的棉絮,有如白雾般虚幻,像捧在手里的一束星星。在触及花朵的片刻,夏油杰的眼前闪过了熟悉的白发人影。
「很美,一朵就够了。小妹妹,快跟母亲一起回家吧。」
教主大人就像个亲切的邻家大哥般,从花束里抽出一朵无根的小白花。他给自己的演技打了一百分,暗暗想着幸运的小猴子,真的没必要杀掉她。
对于夏油杰而言,雨天并不能勾起太多好的回忆。俗话说时间就是金钱,像他这样的大忙人,总会在雨天失去自己的时间,但有也时会得到额外的小事物,例如小猴子给他的一朵小白花,以及被雨势拖住了脚步,看到雨中的街景。
「那么,在妳枯萎之前,我们上哪儿去?」
等离开多金信徒的豪宅之后,夏油并未把无辜的小白花捏碎,而是很随意地把染着水珠的花朵插在直缀的领口。雨仍在下着,那些愁绪甚至穿过斑驳的油纸伞,打湿了他的发梢与肩膀,再次稍微绊住了他的脚步。
(诅咒这种东西,无论多少都能咽下去。雨天的愁绪若是最原始的诅咒,也早该咽下去了。此刻的预感究竟为何物?)
带着小白花的教主步出郊区的豪宅,他让雨珠渗进足袋里,没打算使用咒灵。然后他打了电话给家人们,在大家的惊呼声中说着要在附近的商务旅馆住一宿,接着又打给旅馆订了套房。
旅馆大厅里挤满了疲惫的旅客,活像一座动物园。夏油的脸上浮现了有点诡异的浅笑,神色冷峻地看着自己的手掌。即使掌握了力量,那是连一片羽毛都留不住的掌心,只适合染上鲜血。
(把这里夷为平地,在雨中看着馀烬袅袅升起一阵轻烟。落下的是雨或是血都无妨,在这样的世界里,走到哪儿脚底都满是污秽。)
就在夏油起了些许杀意的片刻,他的身边飘过一股怀念的香气,就像是旧校舍里的书香,却又带着雨天的潮气,席捲了他的呼吸。
「别动。不然我会贯穿你的心口。」优美而坚绝的声调有如雨丝,拂过了夏油的耳际。
「唉呀,真是奇遇呢。」夏油摊手,宽大的衣袖垂在身体两侧,做了个「拿你没辙」的姿势,他侧首向身后的人微笑了下,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?」
「只是路过,顺手阻止你做傻事罢了。」
「真不巧,在贯彻大义之前,我不打算停歇。」夏油闷笑了几声,将带着水气的黑发拨至耳后,「我们到外面聊聊吧,悟。」
这个瞬间,五条差点本能地点头了。不要说去外面,去天涯海角也难不倒他。尽管如此,他已不是十七岁的少年,是该盘算一下如何回答。
「雨势变大了。」五条的脸色比雪更白,竖起的白发加上缠绕住双眼的绷带使他白得渗人,他慢悠悠地说着,微温的指尖触及了宽厚的背脊,「(想要杰留在这里……)有什么话,就在这里话说。」
那水点似的指触让夏油怔了下。除了那两句有点冷冰冰的拒绝以外,他听到了小声的央求。
「呐,五条老师,」夏油把左手放在肩上,带点试探性地做出准备握手的动作,「若有难以启齿的困扰,请把手递过来,让在下为你消灾解惑。」
「教主大人,」五条低声笑着扯下绷带,毫不犹豫地把手递过去,在掌心中凝聚咒力,「帅哥五条老师今天也很烦恼。那么,究竟是谁的错呢?」
「不是吧,悟,这里很多猴……咳咳,很多非术师。」
黑发的诅咒由掌心中放出一只娇小的鮟鱇咒灵,咒灵张开布满细小尖牙的嘴,贪婪地大口鲸吞闪着蓝光的咒力。
「哦,又有新咒灵了。」五条固作惊讶地睁大双眼,白皙的指尖逗弄着鮟鱇咒灵紫色的鱼鳍,「小家伙,我是五条悟,将来要取杰的性命的人。」
「哈哈哈……悟,如果那一天来了,我等着你,直到我咽气。」
夏油收回了咒灵,紧紧地握住五条的手。后者不可置信地看着两人交缠的十指,垂下雪白的眼睫毛,面上浮现了动情的浅笑。
「杰(我爱你),你订了套房对吧(一直爱着你)我们去房里。怎么不答话?你约了别人?(救命,这个色魔教主,非要等他挂了才会属于我?该不会到处乱搞,夜夜笙歌?)」
这一刻,夏油脸上的表情有点扭曲,他简直有口难言,只不过订了一间套房,就被昔日的挚友当成了色魔。至于五条内心不断出现的小声的「爱你」,暂时被他当成了幻听。
只见夏油又好气又好笑地转过身去,想瞧瞧五条一脸促狭的笑容,没想到对方竟然绯红着脸,小声说着:「这么大个人了,还别别扭扭地不答话。我走啦,留给教主大人愉快的情色周末夜(果然夜夜笙歌,想杀了他。)」
「悟,我的情色周末夜不能有你么?怎么,你不敢上楼了?」
「你已经耳背了吗,色魔教主?我.刚.刚.就.说.了.去房里。」
看到五条精致的轮廓结了一层冰霜,夏油的面上却浮起了愉悦的假笑,活像一只得逞的老狐狸。
关于被当作色魔这档子事,他觉得去他妈的解释。既然还在对方身边,就不需要解释。毕竟那对于两名成年男子而言太尴尬了。
*
两人办理好住宿登记,拉拉扯扯地来到二十七楼的五号房,五条进门后一面脱鞋,一面咕哝着往床上一坐:「来啊,你有什么不能给我看的?」他迎上夏油的视线,同时打量着房内:「太冷清了吧。邪教饮精派对在哪?」
「要让你失望了。」夏油又露出狐狸似的笑脸,随手解开了脑后蓬松的丸子,坐到了气鼓鼓的挚友身边,如往常般勾起了唇角,笑道:「你给我办一个吧,悟的脑袋里面才有大型饮精派对啊。」
「……!!?!杰、嗯唔!」
五条一惊,甚至没能推拒对方袭捲而来的热吻,他茫然地想着不是该有很多懂一点术式的漂亮姐姐,大家用酒杯分享教主的宝精,然后开始疯狂的杂交派对,那会是多么淫乱的群像啊。而且教主真的不会精尽人亡吗?该不会用些蛋清制作的假精液来糊弄过去吧。
「咚」地一声,夏油的额头碰着了对方的前额,低声说着:「不行,看来要先把这些妄想赶出悟的脑袋呢。」
「好疼,你干什么啦?」五条白了他一眼,小声说着:「怪了,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?好厉害,教主还能负责通灵?」
「先静一会儿。」夏油吻在刚刚碰着了的位置,取下了领口的小白花,把它放进了五条的掌心,然后吸了一口气,「从现在开始(有点尴尬……),悟肯定会想杀掉我(是悟的话,总觉得能接受。)就是被回忆舍弃的我,也有点紧张起来了(我爱你……爱的场面真令人尴尬。死得其所还比较轻松。)」
(什么?这是!?……是杰的内心话。唔哇,这个闷骚浏海!)
这个念头闪过五条的脑海,他盯着掌心里脆弱的小白花,想着还是别再听了。什么爱啊死啊的,只会让人心变得脆弱。明知如此,听到心上人的告白,他依旧禁不住红了脸。
(想再听一点点……不,还是还给他吧。)
「杰,这是被蜻蜓停过的薄雪草。」五条苍白的面容有了血色,他依偎着夏油的肩头,隐藏面上的红晕,细声说着:「拿去,我不要偷窥你的心。」
「原来如此。」夏油把小白花放在床头柜上,然后他腾出手来,把五条揽紧了些,「蜻蜓是日本传说中的『胜虫』,招来胜利,带来幸运。欧美传说中蜻蜓是逝者的灵魂,有些民间故事则说牠们曾经是龙,能看见他人的内心。」
「嘿,曾经是龙啊。这让我联想到虹龙。」五条粉润的唇角带着笑意,毫不扭捏地问道:「你听到我的内心话,仍然陪着我,我很开心。」
「呵,悟才是很厉害,这么忙啊,一面害羞一面坦白。」夏油的棕眸变得柔和了些,他侧首亲吻那白里透红的面颊,解开对方的上衣,手掌复上白皙的左胸,揉捏了下,「话说你不想偷亏我的心,让我有点受伤。」
「一下子把手里的Big Surprise全部摊开,对心脏不好呢。即使不打开,那些绝望与希望也全部属于我。」五条湛蓝的双眸眼波流转,他抚上了对方的右手,将它压向自己的心脏,「呐,杰,虹龙已经不在了。但是我们共处的时光确实存在,抱紧我,像拥抱青春的回忆那般。」
「真是的,别把人说成潘朵拉的箱子。」夏油苦笑了下,揉了揉五条毛发蓬松的脑袋,「悟,听好了。」夏油的手掌包复住温热的裸胸,感到挚友的心脏在他的掌心下弹跳,他细密地吻在对方的眼睑上,微凉的薄唇抚过雪白的睫毛,「我拥抱的是你,不是回忆。不行呢,被你的双眸注视着,变得什么也想为你做了……」
事已至此,五条无法再听下去。他也想为对方做到一切,在雨停之前,填补属于两人的温存时光。他半闭着眼吻住了向来话多,却很少说真话的挚友。
人生这条路看似漫长,实则苦短。是一条通往所爱之人身边的道路。无论怎么走都无法避开最后的结局。如果在他们之间能看到永远,必定会闪烁着暧昧的微光,走到尽头也不曾熄灭。
那么,就稍微绕一点弯路吧,继续待在彼此身边。白发青年这么想着,不由地紧紧攀住汗湿的蜜色背脊,放任自己喘出声来。
动情之时,夏油咬在五条浑圆雪白的肩头上,亦将那柔嫩的颈项吸啜出红痕,五条的长腿交叠着夹在对方的腰部,淫叫着扭腰摆臀,恨不得成为夏油体内的血液,可以走遍他的全身,一齐痛快奔流。看尽他所编织的理由,那些疏离的温柔,带着悲伤的冷漠,以及无法磨灭的爱意,此刻也充盈在自己胸中。
「杰、杰……再多给我……呼啊、好深、啊啊!!」染上樱花色的指尖在坚实的背脊上留下抓痕,潮红的脸上涕泪交流,透明的津液顺着下颚滑落。
「呵,这方面完全没变呢,贪心的家伙。」夏油轻掐着微微挺立的乳尖,直到那红润的蓓蕾凹陷进去,湿润的嗓音触及对方的耳廓,「你这里特别敏感吧,如此可爱……现在就给你、全部给你,悟……!」
白发青年有点茫然地睁眼,湿润的六眼锁定说他可爱的挚友,害羞地想着这有点恶心,但是好棒,他们还能如此水乳交融。不管是过去、现在,甚至是未来,再也不会有更令他沉醉的一刻──
虽然有点晚,那个总是有点冷冷的夏油杰答应把全部给五条悟了!
「欸,杰……再说一遍、再说一遍。」五条撑起身子,艰困地在床上爬行,好不容易才构着了自己扔到床下的上衣,从口袋里摸出手机,「好嘛,再说一遍『现在就给你、全部给你。』我要录音♪」
「被你这样闹,我有点萎掉了。」嘴上虽然抱怨着,夏油愉悦地笑了。他注视着挚友写满期待的星眸,对着手机说道:「悟,如此可爱。一直都很可爱,今天特别淫乱又可爱呢,现在就给你,过来吧……全部给你。」
「这、杰,你……」五条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,手上还捧着手机。
「得了吧你。」夏油从目瞪口呆的情人手里拿过手机,关掉录音摆到床头柜上,态若自然地下了指示:「来,乖乖地把臀部转过来,我还没完事。」
「色魔教主……你要的屁股在这里啦!」
受到挚友如此调戏,白发青年噘了噘嘴,咬着下唇把臀部凑近了对方面前。两瓣臀肉上还挂着汗珠,中间的缝隙还分泌出透明的肠液,混合着浓浊的精液,看上去十分淫荡。
「悟,当老师的人总该知道『气氛』两个字怎么写吧?」夏油往对方屁股上重重拍了下,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调笑。
「囉嗦……嗯啊、这样、掰开,屁股会、阖不拢的!……啊呜、杰……」
五条在被夏油重新插入的片刻,语气明显地软了下去。他喘息着,心里抱怨对方根本就没有萎掉,却又禁不住摇晃动着腰部,将带着五指印的雪白臀部凑近对方,渴求着所爱之人。
「没错,更加地、渴求我,悟……」
「杰、啊、我要你、我要你……太激烈了!呀啊、嗯啊啊啊!!」
正由背后挺进的夏油含住了五条的耳垂,扣住对方酸软的细腰,硬挺的龟头磨擦着湿润的肠壁,深掘着炙热紧窄的体内,每一下都撞击在对方的敏感点上。五条叫着夏油的名字,射了出来。
在这个诸事不顺的雨天,两人手边没有正事,抛开成人的束缚,在旅馆的床上开始彼此掠夺,耳中只有彼此的喘息与心跳,几乎想把对方吞进肚里,直到一根手指都抬不起来,就这么互相依偎着,阖上了双眼。
事后,五条被自己的腹鸣声吵醒,他瞥了眼睡在身边的夏油,有点不敢置信地眨了眨眼,他伸手一摸,自己身上不知何时被盖了一条毯子,贴身的衣物也被更换过了。
这种事并非初次发生,在高专时期他们好几次做到累了,就两人依偎着一起睡着了。其中只两、三次夏油帮五条更换衣服,并且帮他清理身体。
「呃,杰这家伙趁我睡着时帮我换衣服……他当我还是十七岁?」
五条冷着脸睐了夏油一眼,怀着奇妙的心情,小心翼翼地从床上坐起。他想打电话叫客房服务,却又注意到地毯上好像有白色的事物,是那朵薄雪草,在他俩尽情亲热时,被震得从床头柜落下来,边缘已经有点枯萎了。
「真可怜,我给你一点水吧。」五条低声对小白花说着,轻轻把它十起,放在掌心里。
「悟?」夏油侧过了身子,一脸睡眼惺忪的表情。
「怎么,你醒了啊。」五条以平日的语气说着,用咖啡杯装了些清水,把薄雪草放进杯中,「我要叫客房服务,想吃什么?」
「噗……是啊,义大利面。」夏油被对方那种不拘小节的少爷脾气逗笑了。他起身时挽了下披肩的黑发,继续说道:「唉,可惜这里没有冷面。但是义大利面我多少能吃一点。」
「杰,这朵小花上面的灵魂已经走了吧。」五条有点突兀地说着,放下了手中的咖啡杯,「我已经听不到你内心的声音了。」
「牠走了。」夏油随手将黑发紮成松松的马尾,「你还没注意到?那是虹龙的灵魂,严格说来是牠身为龙时的灵魂,在失去力量后附在蜻蜓上面。可以说是『虹龙的报恩』吧。」
「等等,虹龙的报恩是什么鬼啦……杰原来喜欢吉卜力这类童话设定?」五条做了个「受不了你」的表情。
「蛮喜欢的,尤其是风景好的几部,感觉很宁静。」
「没想到你会这么认真回答。对了,我打电话叫义大利面。」
「请吧。我去洗把脸。」
雨不知何时停了。云雾密布的夜空中似乎浮现了虹龙的身影。白发青年看到十七岁的自己咧嘴笑着,愉快地乘坐在通体透亮的金眼龙型咒灵上,身边还有紮着高丸子头的恋人,两人战无不胜,攻无不克,笑得一脸狂放不羁。
(谢谢你,虹龙。杰目前过得不错,我也……嗯,有点忙,姑且算是还好吧。请在天上照看着我们。请让我能陪着杰直到最后一刻。)
白发青年在心里默默祈祷着,拿起了话筒。
FIN